前言:
20年前我第一次去西藏旅行,足足转了五十多天。
从阿里无人区出来后,我在日喀则止步;我要在那里等朋友给我寄美金,因为我忽然很想继续独旅尼泊尔。
在等待美金的那几天,我天天在日喀则随意晃悠;然后写了一篇游记,顺手扔到旅游论坛上,游记名叫《日喀则,我只是个路人》。
后来该旅游论坛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合作,出了一本背包客游记的书——背包客当时都被称作是“驴友”,于是书名就叫《“驴”行天下》。

书中收录了老非的两篇游记,其中一篇就是《日喀则,我只是个路人》;全文如下。
顺便说一句,该书的编辑之一@稻糠,现在也在头条玩,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扔点东西,看上去兴趣索然的样子。
可在当年,包括他在内的这本书中的驴友,每一个都是背包客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人物。
他们当年走过的风景,趟过的路,写过的游记,现在都依然存在。
只不过当年人们的阅读习惯,不像现在这么快餐化、碎片化和娱乐化罢了。


1,
有一种生活是飞:飘来,飘去。
如果我注定是一个收不住自己翅膀的人,那么飘来飘去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真真切切、踏踏实实的生活。
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晒着高原的太阳,暖融融的味道慢慢浸润了整个体腔。这个时候我的体腔纤尘不染、无比空旷,像是可以盛下整个世界。
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。
这是日喀则,西藏。
我定定地坐在那儿,看一双双纤足在大街上闪烁,她们行色匆匆,怀揣着各自的世界,对我视而不见。

在这段生命切片上,整个世界都对我视而不见。
这让我无比的安静。
陌生的城市,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人们一如既往地在这里生老病死,我一如既往地从这里飘来飘去。
这是他们的城市,他们的生活空间;只是我的一个驿站。
日喀则,我只是个路人。

2,
游荡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肤表,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。
没有人知道你,没有人在乎你;没有人因为你笑了才笑,也没有人因为你悲了才悲。
反过来也是一样。
小乞丐冲我伸出小手,我也笑呵呵地冲小乞丐伸出我的手。
老喇嘛和蔼地对我说“扎西德勒”,我也毕恭毕敬地对他说“扎西德勒”。
小饭馆的老板娘在我付账的时候客气地道声“谢谢”,我也在起身走人的时候道声“谢谢”。
小酒吧的女招待在我喝完最后一杯啤酒的时候道声“bye-bye”,我也在晃晃悠悠地走出小门的时候道声“bye-bye”……
然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。
路人只是从一个驿站掠过,和一个城市相切;不大可能走进一个城市。
不走进,这个城市就不可能会让你爱恨交加。
我因此身轻如燕。

3,
十年前,一个喜欢出走的女孩子对我说:“人的魅力有时候就在于自己不被城市所征服的那一份自然。”
她一直蕴含着这种自然,在我的面前不经意地晃呀晃,结果我扑通一声,掉进了第一次爱情。
集合了人类文明顶峰要素的城市,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附带着湮灭自然的性质。在这里,我们渐渐地忘记了什么是蓝天白云的白昼,繁星满天的夜空。
在这里,自然的自然节节败退,人们的自然渐渐萎缩。
人们似乎必须接受被定型生产才能够适应整个社会,因此必须隐藏自己的自然、压迫自己的个性。

我喜欢北京,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北京人。
我认为自己仅存的那一点自然弥足珍贵,于是,那个时候我一边适应城市,一边莫名其妙地和城市做着顽强的对抗。
走的地方多了,我才知道什么叫做“被自然感动”——被自然的自然感动、被自己的自然感动。
我因此迷恋出走。

十年过去,一个出走变成了生命惯性的女孩子对我说:“我总是轻薄了城市的风情;现在我知道爱远方的土地,和爱我生活的城市是一种爱。所以我去远方,所以我又归来。”
这是我遇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智慧女孩,下载她成为我最好的异性朋友,成为我多年网络生活的最成功之处。
我们渴望在文明的顶峰节点上生活,可是我们的祖先毕竟是从自然界裸身奔跑而出的。即使我们进化掉了自己的尾巴,我们的天性中依然保留着对于自然界天然的亲近感。
还有我们的那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然,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
只有自己的东西才可以真正交付。
因此,我所向往的爱情,必须彼此交付自然。

我安居。在城市里兑换生活的凭借,是我的蛰伏期。我珍惜这种生活。
现在,我出走。
飘来飘去的时候,是我的激情种子向着亮丽的阳光一次性怒放。
我热爱这种生活。
我存在着,在城市也好,在自然也好。
我生长着,不管是安居,还是出走。
都一样。

4,
傍晚我从宾馆房间的窗口看出去,远山一片金黄。
日喀则民居的屋顶静静地铺陈在夕阳之下,一直延绵到城市的边缘。偶尔,从某个不知名的小巷子里面传出一两声自行车铃响。
抬头望天,一朵朵鲜红的云彩缓缓地飘过去……
我久久地站立在窗前。
那种感觉就像是喝醉了,但是死活也还是不愿意放下手中的酒一样。
明天,我将告别这个驿站。
关注@老非2020,分享旅行。
文字原创;未经本人允许拒绝任何转载!
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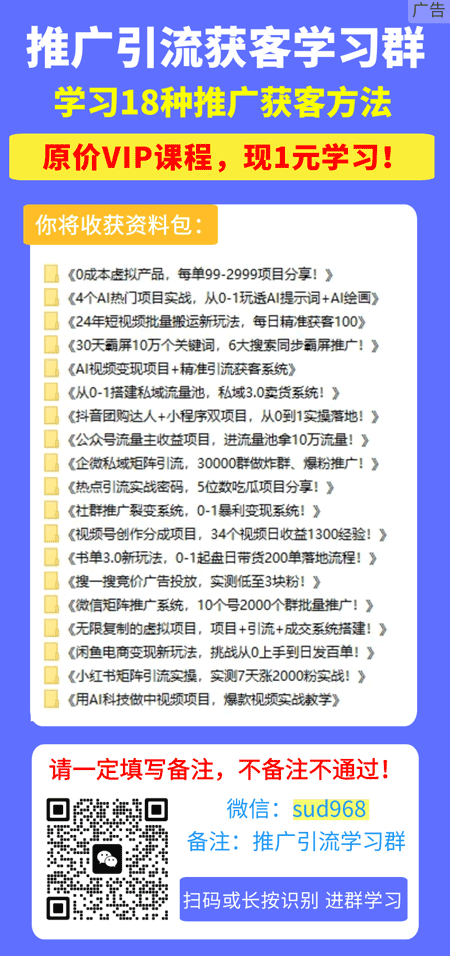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summeng.com/2946.html
